那天晚上,我坐在堂屋的八仙桌前,手里攥着一支旧钢笔柚木提娜种子,目前的白纸上写满了密密匝匝的字。 屋檐下的灯泡昏黄如豆,摇曳的光影映在墙上,仿佛一张张嘲讽的面貌。 窗外的风搀和着冬日的寒意,呼啸着撞击着屋门,像是在催促着我作念出决定。 草榴电影 夫人春梅站在一旁柚木提娜种子,满脸忧色,声息低千里却带着一点苦求:“开国啊,你再思思看。98万给志强,2万给志远,这样分确凿稳当吗?志远亦然我们的女儿啊。” 我皱着眉头,敲了敲桌面,口吻里带着一点抵制置疑:“小梅,我们家这点家原来来就未几。 志远终年在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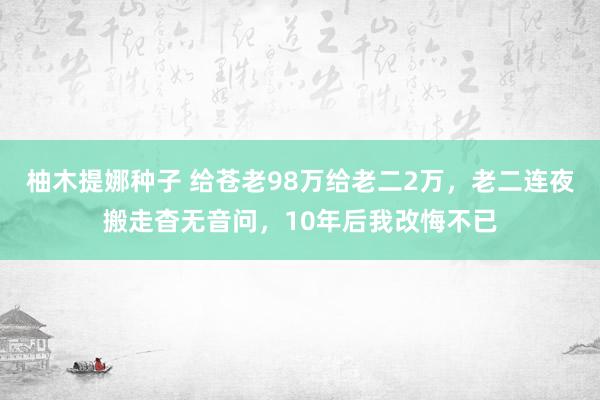
那天晚上,我坐在堂屋的八仙桌前,手里攥着一支旧钢笔柚木提娜种子,目前的白纸上写满了密密匝匝的字。
屋檐下的灯泡昏黄如豆,摇曳的光影映在墙上,仿佛一张张嘲讽的面貌。
窗外的风搀和着冬日的寒意,呼啸着撞击着屋门,像是在催促着我作念出决定。
草榴电影
夫人春梅站在一旁柚木提娜种子,满脸忧色,声息低千里却带着一点苦求:“开国啊,你再思思看。98万给志强,2万给志远,这样分确凿稳当吗?志远亦然我们的女儿啊。”
我皱着眉头,敲了敲桌面,口吻里带着一点抵制置疑:“小梅,我们家这点家原来来就未几。
志远终年在外打工,家里的地少量没种,屋子也没住,凭什么给他多?
志强是宗子,这些年守在家里,种地养家,关注咱俩,没少受罪。

给他多一些是应该的。”
春梅叹了连气儿,眼圈有些发红:“可志远会何如思呢?他会不会认为我们偏心?他还年青,一个东谈主在外闯荡,该有多孑然……”
“孑然?他年青力壮,吃点苦何如了?”我打断了她的话,口吻有些硬,“分家产这事,拖了这样久,今天必须定下来!”

说完,我提起笔,在分家的告示上签了名字柚木提娜种子,然后“啪”地一声将笔摔在桌上:“就这样定了!”